月下,一個黑人坐在沙灘邊,看著大海。那是一雙深邃的眼,眼裡散發著難言的憂傷。
躺在潮濕的沙灘上,他決定閉上眼,等待死亡。
他來自於一個非洲部落,雖說是部落,但大多時間裡留下的記憶只有打殺。人們不僅僅戒備野獸和敵對部落,還有一些他的一家人,半數死於部落間的衝突。
死人是常有的事,即使沒有戰爭。
他才懂事不久,一支由外鄉人組成的名為「希望」的考察隊帶走了他,還有一些和他一樣的同胞們。 他甚至還沒來得及同母親、父親告別就匆匆離開了。
他隱約記得,自己被帶去的地方叫美… 堅… 國… 去他媽的國。當被帶入那是個該死的白到無瑕的房間,他還以為見到了「神明」—— 部落尊崇白色。他用部落的習俗以示尊敬,甚至於幻想出了美好的未來。
那才不是他媽的 「神明」,而是「White Satan」。
當他轉過頭時,瞳孔下意識地縮小,他看到自己的右邊有無數的白床和死屍,黑色與黃色夾著森森白骨一一唯獨沒有白色。
因為神明,早就拋棄了世界,真理?公正?是要財物買的!
他想起一個基督教神父的話「去他媽的上帝!」
他在一次手術後,被迫注射了許多生物試劑。隨著身體上出現的劇痛與各種不適,他才明白,自己是實驗品,哦不,學會 “白撒旦” 的語言後,發現他在他們心中與動物無異。
他活了下來,不知是否是幸運,因為他是少數幾個可以靠自己的免疫對抗新型病毒的人。
他睜開眼,夜晚的嚴寒終止他的思想。寒冷給他帶來的痛苦早已不算什麼了,放在平時,他是不會在意的。
「太空曠了嗎?」他不禁問自己,「不能睡。」
他在某一次押運中,和同胞們計劃逃離,但是結果似乎不盡人意一一隻有他活著離開了。
到了社會上他發現有許多同他一般的,以其他方式來到這個地方的同胞,他們之間非常容易辨認 —— 皮膚黑得顯眼。白人排斥他們,惡毒地稱他們為「野獸」。他不理解:明明他們才是野獸。
同胞們常有不公正的待遇,不只他一個人是這樣。
他是善良的,至少在踏上北美洲之前。
他在一次「機遇」中,看到了白人槍殺了自己的同胞,不安的血液沸騰了起來,開始了第一次小規模運動:去五角大樓。
他第一次感受了領導的快感。 他成為了南美洲巴西里約熱內盧「紅色司令部」的干部毒販,他看清了社會,人命在他眼里分文不值。
他脅迫神父說違背信仰的話,打碎他人的「信仰」。
從販毒開始,誰也沒有人性。
他以為世界上還有一絲善良是他見到了她,他和她,相遇,相愛,可回頭時,她被自己的商品 “殺害”。
美國,生物實驗室病毒洩露,新病毒越來越不受人類控制,肆意踐踏人命。而現在,這片土地隻大概剩他一個人…… 或生物。 世界是死的。 貧瘠的土地,遍地的屍體,空氣中的惡臭,海水的血腥。
他想起了他的新名字「Yohann」—— 上帝是仁慈的。
可人類是自取滅亡的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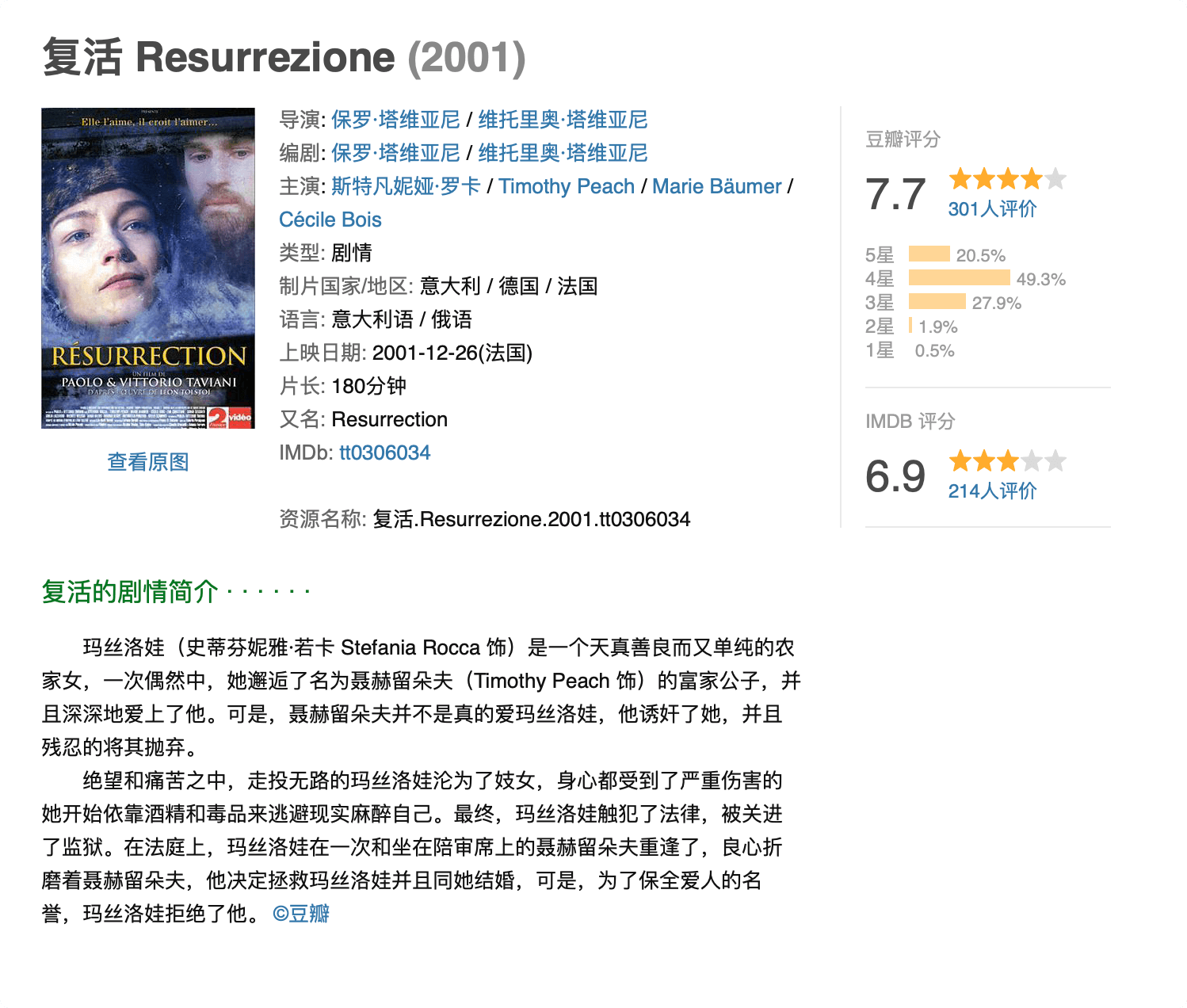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.png)
B站就是这样,害…